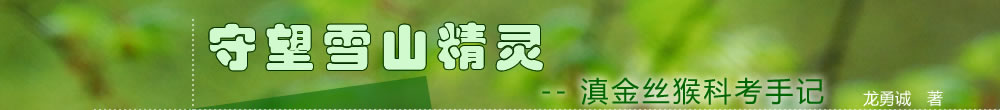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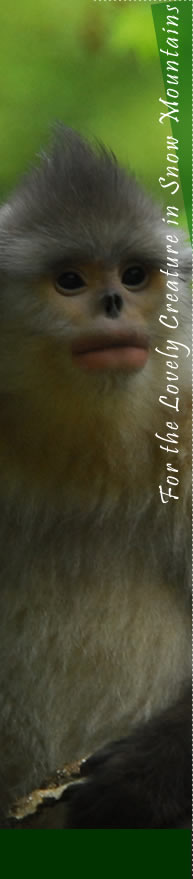
对这个保护区,我早已十分熟悉。我曾在1985和1986两年间,长期蹲点在这保护区内从事冬虫夏草的人工培育工作。所以对保护区管理局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已经混得很熟。 一到保护区管理局,我马上去找局长董德福。老董是1963年就来到德钦工作的一位外地汉族干部,在过去长期从事林业工作生涯当中,雪山上的风霜早已把他变成了一位地道的“德钦人”。他为人真诚、待人和气,也是我过去在德钦工作时的一位故交。 我跟老董寒暄了几句之后就直截了当地把我这次的意图向他摆了出来。老董当即表示十分乐意与我合作在保护区内进行滇金丝猴的长期生态行为学研究,并征求我的具体意见。我马上提出:先请老董先委派保护区管理局的技术骨干忠泰次里协助我上山去选定这一地点,待这一地点定出来以后正式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后,我再考虑是否要管理局增派人手,协助工作。对此,老董一口就答应下来。马上把忠泰次里叫来,和我一道商量上山选点的具体事谊。 其实,忠泰次里与我早就是朋友了。1987年底,他曾陪同我到他的家乡——德钦县佛山乡巴美村调查那里的一个滇金丝猴群。 他为人忠厚、实在,给人的感觉是:任何事情,只要交待给他,你就用不着再去为之担心了。我俩都属羊,但在岁数上,他比我刚好差一轮,我当时已经虚度35个春秋了,而他则刚步入青年。他皮肤黝黑,身高1.80米,显得十分魁梧、壮实,一看就是地道的藏族小伙子。但实际上,他并不是藏族,而是被藏族同化了的纳西族。对此,我还是那次在他的家乡调查滇金丝猴时才知道的。 据说,整个巴美村和与之相邻的西藏芒康县的盐井乡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古代随当时的丽江纳西族首领木天王进军西藏所留下来的后代。他们除仍保留自己的语言以外,在生活上已全部藏化了,并且每个成年人都能说流利的藏语。此外,他们的名字也全部是藏族名字。如:忠泰次里的藏语意思就是叫化子。忠泰次里的爸爸——巴美村的老村长告诉我,在忠泰次里出生之前,他的妻子已一连生了三胎,可惜连一个孩子也没带大。所以一生下忠泰次里,就取这个名字,为的是希望能把他顺利养大。 经过一番商量,我们认为现在只有两个可选的猴群。一个是义用村后山的猴群,另一个是吾牙普牙村后山的猴群。 |
